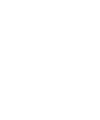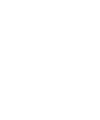贵极人臣 - 第127节
三丫低头一瞧,碟子中是一碟花生米,白瓷杯里是白水。小孩子心里藏不住事,她磕磕巴巴问道:“李父母,您的铜板呢?”
月池失笑:“都花出去了。”
花了?三丫不解道:“您是买田了?”
月池摇摇头:“不是。”
“那您是买新宅子了?”三丫歪着头又问, 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,“您马上就要搬家了是不是, 我爹说了,哪有老爷一直住在庙里的,您的新家在哪儿呀……”
眼见小姑娘叽叽喳喳个没完, 月池忙打断她道:“别说我了, 说说你们家。你的小妹妹, 还好吗?”
三丫一愣,她道:“好,自有叔伯被抓了后,爹再不敢再把妹妹丢进河里了。他们把不想要的女娃都送到了一个院子里,那院子叫、叫……”
月池接口道:“育婴堂。”
“对对对,就是育婴堂。”三丫挠挠头,“我不认识字……记不住。那里面好多小娃娃,都是在哭。我悄悄看了,都是妹妹!”
月池淡淡道:“舍得溺毙男婴的,毕竟是少数。”
三丫道:“对,我爹说了,女娃是赔钱货,生多了没用,就只有丢进河里。”
三丫话音一落,就听李父母道:“别听他们瞎说。你……”
月池对着三丫懵懂的脸,半晌方道:“你得爱惜自己。别人都看不起你,都嫌弃你,你再不珍惜自己,就只能像小黑一样了。你想像小黑一样没命,被埋在黑漆漆的地里吗?”小黑是指母猫所生的那只小猫崽,因为太过瘦弱,出生不久就去了。
三丫慌乱地摇摇头,月池摸了摸她的头:“这就对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架织机。等你想学手艺了,就可以持我的手信去育婴堂找师傅了。”
三丫惊喜地睁大眼,此世妇女谋生靠得多是织布的手艺,会织一手布,不仅能解决自家的穿戴,还能换铜板。她想跳下来凳子磕头,却被月池拦住了。
月池道:“不必客气。把猫儿都带回去吧。最近要锁好门,不要乱跑,知道吗?”
都带回去……三丫愕然抬头,月池缓缓道:“它们都长大了,都能去抓老鼠了。我已经有马陪了,就把它们都还给你吧。”
母猫是愿意跟着三丫去的,可小猫们却与她不甚熟悉,它们在院子里乱窜,不肯离开。最后还是秦竺、柏芳等人合力,才将这三只小崽子逮住,塞进了篮子里。三丫木木呆呆地拎着篮子,小猫在篮子里叫得一声比一声凄凉。她虽然不解何事,但也能察觉到气氛的变化。她刚刚走到院门口时,就噔噔蹬地跑回来,她气喘吁吁地立在月池面前:“李父母,我以后还能来看您吗?”
月池笑道:“当然。”
三丫一下就笑开了,她又道:“谢谢您给我织机……那以后,等我学会了织布,一定给您送一身簇新的衣裳!”
月池莞尔,她有心回绝,到底不忍拂了小姑娘的心意,她笑道:“我等着三丫的新衣裳。”
三丫喜笑颜开,蹦蹦跳跳地走了。她走了之后,院中又重归寂静,月池又开始发呆。时春去练雇兵了,刘瑾去组织民兵了,葛太医在协助调配梨花枪中的毒药和金疮药,锦衣卫们大多在四处打探鞑靼方的消息,只有她是无事可做。
监察御史曹闵刚到宣府,所有人就要借机停了她一切的职权,还要遣散雇军。幸好,曹闵是她在都察院中的同僚,又是个清正的明白人,并没有赶尽杀绝,只是让她在东岳庙中候旨,雇军、军马、军械到底保留了下来。她抓住这最后的机会,严惩溺毙女婴的父母,散尽家财建起育婴堂,收容被遗弃的婴孩。到最后,钱花光了,她也只能枯坐了,毕竟她可是连书都卖掉了,一本不留。她正昏昏欲睡间,忽听到嗒嗒的马蹄声。
她惊诧不已,刚刚睁开眼,就见秦竺牵着一匹黑马立在庭院中。月池问道:“这是作甚?”
秦竺亦是不解:“不是您说,想要马来陪……”
月池一时无语,哄小孩子的话,竟然被当了真。秦竺也知自己是关心则乱,一时犯了傻。他想把马牵走,马却不乐意了。这匹马在这些日子里,顿顿有黑豆,到底贴上了些膘,也认识了时时来喂它,给它牧草和黑豆的人。它一见到月池,再不复当时的畏惧冷漠,打了个响鼻,撒着欢就要奔过来。秦竺一时都有些拉不住。月池失笑,她忙道:“快站住。听话。”
月池原本只想摸摸它,可看它尾巴直摇,不停往她怀里蹭的模样,一时就想起了大福。她暗叹了一声,要了刷子和水,竟是要替马洗澡。秦竺吃了一惊,他只是想替李御史解闷,可不是让他如此劳累的。他道:“御史,您是千金贵体,这是马夫干得活……”
月池道:“马夫至少还是良民,我已是待罪之身,本就不如马夫。”
秦竺跟了她这些日子,何尝不知她的脾气。他不敢再拦,只得从命。月池拿着刷子,把这匹马从头到脚,都断断续续刷了一遍。马儿也不嫌弃她动作慢,就乖乖地立着,被这么一拾掇,竟有了些精神奕奕之感。月池摩挲着它身上纵横交错的伤疤,不住地夸赞它:“真是一匹好马啊。你们可比人好多了。”
秦竺在一旁欲言又止,月池见他仿佛便秘的神色,不由扬了扬眉道:“我又没说你。你们虽是碍于皇命,可做事却也尽心。”
秦竺一愣,他不敢置信道:“您都知道?御史,即便是万岁不下密旨,我等也会为您好生办事。人心都是肉长得啊,您对我们委实是亲厚……”
月池翘了翘嘴角:“我不过是按劳分配,论功行赏罢了,是你们其他上司太不是个东西,才把我显了出来。”
秦竺苦笑道:“可这年头,不是东西的上司才是多数。这世上,唯有万岁和您,算得上宽厚悯下。”
朱厚照宽厚悯下?月池没有答话,秦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完成圣上嘱托的机会,只得硬着头皮往下说:“万岁对您,就委实不薄。”
月池霍然看向他,她的目光如电,逼得秦竺低下头去。月池丢下刷子,进屋去沐浴更衣。秦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,在外头乱窜。待到用饭时,他还在继续劝说:“即便到了今日这个地步,万岁还是在尽力保住您。监察御史曹闵为人方正,不会为难您。只要您在宣府之战中保全自己,圣上就有法子保住您的性命。届时您再去积累功勋,为民请命,步步高升是指日可待,这样看来,您的前路依旧光明灿烂,又何必要往窄处走。您、您就一点儿不顾及金兰之契吗?万岁说,即便有一百步的距离,他已经竭尽全力,走了九十九步了,您就连一步都不愿跨吗?”
月池放下了筷子,碗筷相碰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她的心情很是烦闷,她疑心自己就算到了阴曹地府都不得安宁。她太明白朱厚照的想法了,他自小什么都有,于是什么都想要。作为皇帝时,他不愿意在权力上让步,作为人时,他又不愿意接受任何情感上的挫折。
他在短暂的挣扎后,就开始想二者得兼。而他的身份,他的脑子,又让他比平常人多太多的筹码。只要他想,他就能有无数的游戏币,可以一次一次在抓娃娃机里夹玩偶,直到夹上来为止。
可他没有想过,那个玩偶被铁钳夹住身体,被往外拖时,又是什么感受。她或许一辈子都无法打破这个抓娃娃机,但她可以选择不被夹上去,她可以选择以另一种方式离开这儿。至高无上的天子可以毫不费劲折断“会思想的芦苇”【1】,可他永远也得不到它。他也察觉到了这点,所以指使秦竺来打感情牌。最可笑的是,他自己都没有把情感放在第一位,又凭什么希冀她会因那一点微末的情分而违背原则?
月池冷笑一声:“顾及又如何,不顾及又如何。顾及情分,猫就能变成老虎,老虎就能变成猫吗?”
秦竺听得如坠五里雾中,月池对着他一片茫然的脸,长叹一声。她将那块殷商古玉,玉鸟形佩取了出来,放在了秦竺面前。秦竺当然听说过这块三千年的奇珍,他还以为李御史把所有值钱的家伙都卖光了,没想到,他还留着这样。可他这时取出来,又是何意呢?
他抬头望过去,只见李御史定定盯着角落良久,当他再抬起头时,目光却仿佛秋日阳光下的湖水,平静到狂风都无法在面上起一丝波澜:“拿去还给他吧。就说,愿圣上万寿无疆,以享永祚,而臣要家去了……无论是玉,还是别的东西,我受不起,也都用不着了……”
秦竺满心疑惑地看着她:“您把家底都搬空了,还怎么回乡。”
月池释然一笑:“我自有回去的办法。”我以此功德敬告神佛,如神佛有知,请怜我思乡之情,请让我从这孽海苦旅之中解脱,请让我回家吧。
玉鸟形佩被层层软布和棉花包裹,放置于锦匣之中,被送回到了东暖阁的案几上。曾几何时,他们也会在日光和煦的时候,在奇楠香的恬淡中,坐在这张炕桌的两侧,专心致志地看书。看到有趣之处时,吃到好吃的点心时,他就会叫他的名字,让他也过来瞧一瞧、尝一尝。
如今,朱厚照摩挲着这块古玉,当年他将这块美玉交给他,允他插手内宫财政。这是他给李越的第一份权力,是李越进入官场的起点。如今,李越却把这块玉还了回来,说他受不起、也用不着了……朱厚照深吸一口气,他几乎是在求他活下来,可他的感情,他的真心,又一次被丢了回来。
他以为自己肯定会哭,肯定会痛哭流涕,伤心欲绝。可没想到,真的到了这一刻,他的心中也是一片平静。他躺在窗边,夕阳金色的余晖给他的脸颊镀上了一层金边,他苦笑一声:“这本来就是李越会做的事啊……”谁都拦不住他了,谁都拦不住了……
三日后,边关急报,鞑靼小王子奇袭宣府。
第232章 客子过壕追野马
真是绝妙好计啊。
明廷是在安逸的生活中日益懈怠, 而蒙古诸部却是在不断的内斗中日益穷困。到了如今,不论是鞑靼还是瓦剌,都无法靠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维持牧民的生计。在弘治年间, 蒙古还可以通过马市, 与边境的百姓进行交易。可是后来,达延汗自恃羽翼已丰, 以大元大可汗的身份自称,对待明廷的态度逐渐骄横。
他在弘治九年时,要求明廷同意,他派遣三千人使臣进京入贡。孝宗爷的脑子又没进水,怎么可能放这么多蒙古人到京师重地, 还要给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,这是既耗费财物, 又提心吊胆。他们要求达延汗减少使臣,派一千人来即可。达延汗却出口威胁:“减我一人,三千人俱不来。”
于是,这一次争执后,双方就彻底闹崩了。明廷开始严密的经济封锁,鞑靼再不能通过和平手段从中原获取财物,他们只能沿着长城一线, 通过入侵抢夺,来获得生活物资。如果不去抢夺, 鞑靼贵族无法维持奢华的生活,而寻常牧民也可能连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。这也是达延汗无论如何,都不肯放弃攻打宣大的根本原因。
满都海福晋却持不同的看法, 她认为达延汗的傲慢自大, 给子民们带来了战祸。汉家王朝不会躺平任他们来去, 他们也会反击,多多少少也会给草原儿郎带来伤亡。目前,达延汗还没有统一整个蒙古,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应该先笼络东边的强敌,通过马市、走私获取物资,等到一统鞑靼和瓦剌后,再挥师南下,在长城一带扩展领地。
满都海福晋不同于深宫中的皇后,她是背靠汪古部,能够马上征战,拥有极高威望的女中豪杰。她的意见一旦与达延汗相悖,是能够对他形成强力掣肘的。可这种压制却让达延汗更加无法领会自己妻子的心意。他是黄金家族的继承者,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,这血脉优势让他和朱厚照几乎是一样的自傲。
可朱厚照是在父亲疼爱,众星捧月中长大,他的性格弱点只是年幼登顶的孤独和寂寞,可达延汗却是在虐待、歧视中挣回一条命,这让他天性敏感,睚眦必报。特别是在面对满都海福晋时,他是既感激爱惜,又自卑忌惮。所以,在满都海福晋越强调他的失败,越认为他不能去攻打宣府时,他就越要和她对着干。
金帐中,两人的争吵一直不断。达延汗的面色铁青,他已经将金帐中能砸的器物都摔得粉碎。他斥道:“好一个英明的彻辰夫人,好一个大哈敦,你永远都是对的,我就总会有错!你既然如此明智,那你告诉我,这已经到了秋季,正是汉人收获的时节,我们要是不去抢夺,我们要怎么保障部民在严冬中活下去,靠你这些假大空的道理吗!”
他的身材高大魁梧,早就不是那个牵着她的衣摆畏畏缩缩的小男孩。满都海福晋从来没有被他这样不客气的呵斥过,她心中不仅有伤心,更有一种压迫之感。她也是多年说一不二,这让她本能地开始反击:“我说了,我估算过,我们的粮草绰绰有余,只要你停止肆意挥霍,一直酗酒。是那些马尿迷了你的心肠吗?让你在这种时候还在意气用事,非要往陷阱中跳。”
“马尿?”达延汗的脸涨得通红:“大哈敦,注意你的身份和礼节,你是在对大元可汗说话!探子已经来报,事实就摆在眼前,李越在宣府一意孤行,早已引起了周边官员的不满,他们巴不得他去死,所以故意漏给我们空缺,借我们的手去杀李越的头。这不是陷阱,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为什么就是固执己见,不肯睁开眼看看。”
满都海福晋柳眉倒立,冷笑不断:“你怎么不提,李越也在宣府募兵练兵,此人诡计多端,他既然敢这么做,怎会没有一二分的底气,难道他会像草人一样立着等你去杀么?你以为自己是捕蝉的螳螂,却对身后的黄雀视而不见。再说了,他是文官,必定不会出城,你难道还想进入城郭中去追杀他不成。大汗,我是怕你,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。”
不能进城去杀李越确实是达延汗没想到的,可他却不愿意服软,还要继续争执:“这短短几月能练出什么来,不仍是一群废物,怎么敌得过我们的铁骑。”
眼见满都海福晋面上怒火更炽,达延汗也不由描补:“战场的情况谁能一口断定,汉人内斗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届时随机应变不就好了,为何要从一开始就打退堂鼓。这哪里是蒙古勇士的作风,只有无知软弱的妇人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”
满都海福晋已然出离了愤怒:“好,很好。大汗既然主意已定,我这个无知软弱的妇人就不再多嘴多舌了,我就祝大汗旗开得胜,满载而归!”
满都海福晋拂袖而去,达延汗被她语中的不屑气得浑身发抖,她仿佛已经看到了他的失败一样。他在她身后吼道:“那就请大哈敦拭目以待!”
满都海福晋的脚步微顿,却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她回到自己的斡耳朵中,屏退左右,枯坐到了深夜。直到夜深人静时,她的眼泪才开始簌簌直流。第二日,索布德公主听闻了消息,一大早就来到母亲的床边,自然也看到了她红肿的眼眶和未干的泪痕。
索布德公主既心疼又不解,她在宣府吃了那么大的苦头,对李越同样也是恨之入骨,是以很赞同达延汗按照惯例在秋收时去宣府劫掠。她对满都海福晋道:“额吉何必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的威风。大汗七岁就亲征瓦剌,他比那些汉人草包,不知道强多少。以前大汗都是百战百胜,上次是我拖了大汗的后腿,这才……额吉,您就别和大汗硬顶了,您难道就不想要那些宝石和丝绸吗?”
满都海福晋气不打一处来,她戳着索布德公主的额头道:“女人要宝石和丝绸,男人要美女和美酒,你们的眼皮子就这么浅,就只能像土匪一样去夺芝麻大的小利,一点儿都想不到大局和大业?”
索布德公主被她的指甲戳得生疼,她捂着头委屈道:“额吉,你在说什么呢?”
满都海福晋看着自己这个无知的大女儿,忍不住长叹一声,她道:“回去吧,不要老是和那些人玩耍,多看着你自己的儿子,不要再来惹我生气了。”
提及儿子,索布德公主的脸色却阴沉下来,她道:“天知道那个小畜生去哪儿了。”
满都海福晋皱眉道:“什么,嘎鲁又不见了?”
索布德公主霍然起身:“就当那小畜生死了算了。额吉,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我又有孕了!”
满都海福晋吃了一惊,她盯着女儿的肚子,真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。可不论她心绪如何,奇袭宣府的计划已然不可逆转。鞑靼贵族们早就有联合发兵,去九边抢夺的先例,这次由大汗亲自牵头,与汗廷亲厚的部落首领岂有不允之理。两万骑兵,浩浩荡荡杀往宣府,其中甚至还有一些重装骑兵。
骑兵分为重装和轻装两种。轻装骑兵着寻常铠甲,用弓箭为主要武器,以轻快灵活见长,常用于哨探和奔袭。而重装骑兵穿重甲,随身携带刀剑、长矛、铁斧等多种兵器,常用于冲锋陷阵。要装备出这样一支重装骑兵,需要耗费大量的生铁。而所有的铁器都是鞑靼人用重金,从明军中的贪官污吏中购买而来。为了财宝,身为官员居然卖铁器给敌军,以方便敌军更好地屠杀百姓,抢夺民财。监察御史曹闵得知敌情,已是满心愤慨:“人心之脏,真是让人瞠目结舌!”
这样大的阵势,宣府这一边也是早就收到了消息。所有上官开始紧急议事。到了顶雷的时候,再也没人说李越这个罪臣没有参与的权力了。
都御史刘达心惊胆战,已不敢作声。月池却坦然道:“有道是法不责众。寻常官吏又怎敢去硬碰硬呢?只有我这样的天子近臣,才能够去捋虎须。刘御史,你说是不是?”
刘达已是羞惭不能语。曹闵到了宣府这些日子,早已将情况了解得七七八八。于私上,他固然能够理解同情李越,可于公上,李越的的确确是犯了大罪。他叹道:“含章,你这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你做出这样的事情,即便是圣上,亦是有心无力啊。”
月池不置可否,她问道:“这一仗,该怎么打,还是议个章程吧。”
总兵官朱振沉吟片刻道:“依我之见,敌军来势汹汹,还是以坚守为要。”
镇守太监邓平道:“可是,也不能不回击吧。敌军来袭,我们不想法子应对,也是重罪。”
朱振道:“只有等敌军散开,在村落中劫掠时,我们才能去各个击破。”
曹闵久居京都,是初次听闻这样的事,他不由吃惊:“可是,这样的话,鞑靼人不是已经在村落中烧杀过了。”
月池摊手道:“是啊,而且我军夺回的战利品,皆是自分了,哪谈什么还给失主。”
曹闵的目光灼灼,直望向朱振。朱振闷声道:“将士们也是人,他们外出来卖命,难道连一点儿好处都不与吗!你们文官既然要站着说话不腰疼,那在发放军饷时就少贪一点啊。”
曹闵反驳道:“休要在此推卸,我们是在说夺民财之事!”
眼见又要吵起来,刘公公作为这里名义上职位最高的人,敲了敲桌子道:“别扯这些有的没的,快说正事。鞑靼骑兵最早明儿清晨,最晚明天半夜就要赶到了,还说这些作甚。”
会场又是一肃,邓平期期艾艾道:“若要不伤百姓,也并非全无可能。只要我们在偏僻险要之处布好阵势,再将鞑靼骑兵引过来,不就好了。”
刘达皱眉道:“引过去?拿什么引?这说来简单,做起来比登天还难。”
邓平没有作声,只是悄悄地觑向月池。刘达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,也定在了月池身上。朱振暗道,这倒是双全之法,既能保证李越身死,又不至于打了败仗,连累自己。刚这么一想,他的心中又浮现愧意,他这样和那些通敌叛国之人又有什么区别,可事到如今,李越不死,倒霉的就是他们啊。
曹闵拍案而起:“你们看李御史干什么!他是文官,只负责监察,这些分明是武将之职,你等怎可擅自推卸?”
邓平嘟囔道:“这不也是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嘛。他要是不立功,回去八成要被斩首了。”
曹闵气急,他目视刘瑾道:“刘太监,你怎么说。”
刘瑾瞥了一眼月池,他道:“这也不失为可行之策。”
曹闵瞪大了眼睛,他本以为刘太监和李越是站在统一战线,可没想到,到了这种关键时候,他怎么突然反水了。刘瑾也是一派坦然地目视月池,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,李越必须践约。月池环顾四周,这里所有人都想她死,不是想让她在这儿死,就是希望带她回去死。她低头捧起了杯子,水的温热透过瓷杯慢慢沁入她的掌心。她低头抿了一口热水,蓦然笑开:“你们,还挺机灵的。真是绝妙好计啊。”
一阵尴尬的缄默中,邓平试探性道:“这么说,李御史,是同意了?”
曹闵不敢置信地看向月池,月池挑挑眉道:“同意,当然同意。我怎么能违拗众意呢?”
邓平的脸一下就咧开了,他连忙将笑意敛下去,急急道:“那就议议怎么诱敌吧。”
朱振点了点头,他正要说话,月池却打断道:“让我诱敌可以,但必须得让我的夫人参与排兵布阵。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