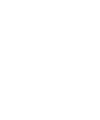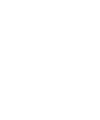贵极人臣 - 第197节
而在他走后, 他设立的预算制和报表制虽然还在进行,可水分却多了不少。谷大用等人也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至于京郊军屯, 一时倒是无人敢占,只是收上来的粮食当如何分配,多少有一些向上偏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 一旦要大规模练兵, 银钱铁定会吃紧。
其次是人心不齐。世袭将官的份额太大了, 兵部以前也想过法子,刘大夏在给朱厚照当面说明了世袭将官的不堪后,就着力去改进武学,严明武举。但正如马克思所说,人不能凭空创造历史,只能“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
世袭将官自永乐后期时,就已经有颓废之象,颓了这么多年,要想叫他们重新振奋起来,不下狠手是不成的。然而,只有真按洪武爷的规矩斗硬,才会有一二疗效,即“令应袭子弟送都督府比试,骑射娴习,始许袭替。”
可即便是江彬不要命去要去赌这么一把,朱厚照也未必会同意,万一这么一考,把人都撵出去了呢?
江彬原以为自己是掉进福窝,谁知是猪八戒照镜子,里外不是人。他不是没想过退下来,凭他的功绩,只要安分守己,倒也能如其他勋贵一般混个平常日子。可一方面是不甘心,江彬的骨子里有一股天然的狠劲在,那么多讨好朱厚照的人,可唯有他在生死关头,能豁出去挡在老虎面前,来博一场富贵荣华,这份心性堪比豺狼。
他已经爬了这个地步,正是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的顶峰,这时反叫他急流勇退,他如何能甘心。另一方面到这个地步,是进是退早已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。他背后站着的是整个边将集团。
随着北伐大捷、宁王伏法,一直以来处于帝国底层的士卒渐渐挺直了腰板。边将与世官之间势必会有一场恶斗。而他的出身,他的地位,就注定他必须站在风口浪尖。
江彬在想透这一点之后,不由饮下一杯苦酒:“什么皇庶子,我看是出头的椽子!铁定先烂!”
许泰叹道:“江哥,事到如今,这头是出也得出,不出也得出。咱们要是主动出,可能是有点磕磕碰碰。”
瘿永补充道:“要是打了退堂鼓,现在就得烂。咱们的仇家都盯着呢。”
刘晖道:“也不必这么揪心。瞧瞧人家李越,他闹成那个样子,不也活得好好得吗?”
江彬道:“那能一样吗?!他和皇爷是什么关系?”
刘晖理直气壮道:“这不都是一家人吗,何必这么见外呢?”
“……”江彬一时真被噎得翻白眼了,神他妈的一家人。
许泰又来了一句:“江哥,咱们沉寂的时间够久了。我们是做臣下的,总不能事事都要皇爷来督促。依我看,上阵亲兄弟,打虎父子兵。”
父子兵……于是,江彬一横心,选在这个关头冒了出来。一则既然恶斗不可避免,那他就先下手为强,先淘汰一拨冗员。二则也算是分担炮火,也算卖李越一个好。果然,他蹦出来之后,骂李越的人又少了一波。
他做得不错,朱厚照当然要予以表彰。朱厚照破天荒地又频频召见他,夸他孝顺懂事。孝顺的“乖儿子”低眉顺眼道:“父皇谬赞了,能为二位长辈分忧,是我做晚辈的荣幸。”
江彬既然要干,那当然就是要干一票大的,不捅一个惊天大案出来,如何能震动朝野呢?
他拿来做筏子的人,名叫石玺。石玺是凤阳人,因祖上的军功,袭了一个武平卫指挥佥事、参将的职位。就是这么一个的参将,却搅得当地民不聊生。他豢养了家丁恶奴数百人,想方设法夺取军民的财产。在他这里,挪用军饷都是小事。他公然设置抽成,命令过往商人都要上他“上供 ”,甚至铲平别人的坟头来为自己修庄园。
朱宸濠作乱后,朝廷查处同党,发现了石玺和宁王勾结的证据,于是将他充军毫州。可没想到,此人真个是手眼通天的人物,人到了毫州,依然能做土皇帝,占人田地,淫人妻女,还杀害了一家人。事发之后,朝廷要将他处斩。他却在公文到之前就收到了消息,脚底抹油跑了。可豪州知州颜木却不是庸碌之辈,他上奏坚决要求处置石玺及其同党,还要亲自率人去追捕。
这桩大案闹了出来,可谓是捅了马蜂窝。江彬说得非常直白:“圣上为天下太平殚精竭虑,我等虽不才,可也为家国安定抛头颅、撒热血。谁知,世上竟有如此凶横忍肆之徒,依仗祖辈的功勋,不思报国,反而在人背后捅刀子。朝廷恩荫百年,怎的反而养出这些贼来!”
这话可谓是难听至极,一众世袭将官,颇为恼怒,就连英国公等人都面露不虞之色,指责他:“难道就只有你一人出力,我们皆是尸位素餐的?”
江彬最后虽然认了怂,表明是自己是粗人,并无冒犯之意,他只是义愤填膺,指责这些罪大恶极之徒而已,却不知道为何大家要抓着这个不放。一众人遭他气了个倒仰,却不好真正为这个与他在金殿上吵起来,只得生生将这口气咽下去。
随后,毫州知州颜木所查出的真相,却将这句话变成了一记耳光,狠狠打在世官集团身上。颜木率人,奔袭至东昌府,将是石氏父子缉拿归案,清查明细后发现石氏父子夺占黎钊等五百余家田产,共三百多顷,房屋一千多间,银两万余两。
这个数目,真可谓是令人发指。月池几乎是立刻就沉下了脸。看来,她去鞑靼的这些年,中央虽然被整治得不敢动弹,可民间却依然有人仗着天高皇帝远为非作歹。
她心思一动,掀袍奏请道:“陛下容禀,刘六刘七作乱时,天下庶民乃至士林中的糊涂之辈,竟将原因归咎于陛下北伐,多征军饷,可如今看来,是这些人不明真相,以致于中了有心人的奸计。国有流饿之民,罪在官有腐蠹之藏!区区一参将,如此肆意妄为,背后必由人相护,如不将国之妖孽连根拔起,圣上圣誉何存,黎民安乐何在?”
朱厚照冷笑一声,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着北镇抚司缉拿审问石玺及同党,务必吐出实话来。”
朝野上下一时寂寂无声,连一根针落地的声响都能听见,北镇抚司专理诏狱,一些特别重大案件,往往北司严刑拷问,锻炼周内,始送法司。这都是圣上的心腹直属,看来,这是要玩真的了。
新科状元杨慎,刚刚点了翰林院修撰,在出了殿上时,才觉得自己的脊背出了一身汗。他四处寻找月池的身影,却发觉她正对五府将官微微一笑。她监了一场春闱,人又憔悴了一些,一身赤袍玉带,更显温润儒雅。可只是这么一笑,却叫一群大老爷们生生打了个寒颤。
杨慎已是许久不见月池,在考试前,他为了避嫌不敢去,而在考后,他则是颇觉尴尬,也不知道同她说些什么。直到出了这档子事,他才找到了理由慢慢挪过来。
只是,真个到了她面前,就要张嘴时,他却突然语塞了。谢丕扑哧一声笑出来。月池也面上有笑意:“怎么,连喊什么都不知道了?”
杨慎哽了许久,硬是没把那一句“座师”叫出口,最后来了一句:“下官拜见李侍郎。”
月池忍不住放声大笑,她道:“可真有你的。说吧,什么事儿,杨修撰这等忙人,想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
杨慎的脸涨得通红,他道:“……我不是故意不来的,只是,这……”
他半晌挤出来一句:“都怪那灯花!”
月池一愣,这才想起,杨慎第一次落榜,就是因灯花烧了他的卷子。如不是灯花烧卷,他必能早一届高中,要是早一届中了,哪还有今日的尴尬事呢?
这话一说,又惹得大家笑将起来。他们一同回到翰林院,笑过之后,杨慎才切入正题。他问道:“能揭穿这桩大案固然好,只是北镇抚司来审问,我总担心,会出岔子。”
他说得还算比较委婉,穆孔晖就非常直了:“锦衣卫榨取钱财,只怕比寻常军官还要狠些,叫北镇抚司去审查,又能查出什么?”
这说的是锦衣卫戕害百姓之事。据说,锦衣卫校尉、军士在京城巡查,将来路不明者,一律当作囚犯缉捕。如有银子的还能用钱赎身,没权没势者就只能被充入苦役。
康海则道:“太祖爷早有训示:‘讯鞫者,法司事也。凡负重罪来者,或令锦衣卫审之,欲先付其情耳,岂令其锻炼耶?而乃非法如是。’”
他们话里话外都是对锦衣卫侵夺司法权的不满,而对她说的原因,则是希望她带领他们想出办法来,把这权夺回三法司。
月池面上的笑意渐渐淡下来。帝国的权柄只有这么多,给了这个,自然就不能给那个。武将希望获得较为崇高的地位,可文官也不愿大权旁落,而皇帝本人更要提防下头,维系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,所以任用宦官和锦衣卫监察文武百官。
至于这些年轻人,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夺权,而认为拿回的是天经地义属于他们的东西。
月池长叹一声,糟糕的是,朱厚照也是这么想的。而这两边使力,都会使到她的头上来。事隔多年,她又渐渐有了做夹心饼干的感觉。
她道: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。”
康海不解道:“圣上对您的看重,世人皆知,只要您肯牵头此案,必能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月池苦笑着摇头:“我毕竟也是文臣。只要是文臣,在这官场中办事,就要逐级上报,层层下达。时间就在这一层层消磨,消息也在一级级别走漏。石家父子如何能在朝廷的公文到达前,提前逃跑?你们有想过吗 ?”
众人一时语塞,月池道:“我们之中的一些人,也并不清白。这叫万岁如何肯信?”
穆孔晖道:“可北镇抚司难道就可信了吗?”
月池道:“北镇抚司至少可以直达天听。由他们去,的确最快。说来,都是同殿为臣,互相弥补,互相监督,才是圣上所乐见的局面。再说了,这次闹得这样大,事关皇上的声誉,即便借杨玉几个胆子,他也不敢做太多手脚。”
杨玉的确是自觉被架在火上烤。他恨得咬牙切齿:“江彬这个王八羔子,真真是好日子过舒坦了,在朝堂放一阵屁,倒把事情全部甩给老子。还有李越,什么事都有他来出头!”
他的下属副指挥使张允叹道:“可偏偏他就是比旁人会出。要是换做六科廊那一帮人,只会嚷嚷民间疾苦,殊不知圣上根本听不进去。可他却直接指向圣上的声名,这一下不就打在七寸上了。”
杨玉闻言一怔,他颓然道:“李越十三岁就入宫,同吃同坐,早已把皇爷摸得透透的。这么一个人,眼中还揉不得沙子,我怕咱们日后的日子也要难过了。”
张允道:“咱们收敛点也就是了。再说了,天塌下来,不还有高个的顶着吗?”
杨玉嗤笑一声:“你敢在皇爷面前充高个儿?”
张允道:“咱们算是哪个牌面上的人,可不还有锦衣卫舍人吗?”
所谓的锦衣卫舍人,是锦衣卫的编外人员,专门任命公、侯、伯、都督、指挥的嫡次子,使他们安享朝廷俸禄。锦衣卫舍人每个月的月粮只有四石,如何够这些纨绔子弟挥霍,他们过去在京中勒索,如今京中风声紧了,就会想办法外放,去地方上打秋风。
张允道:“要是真闹起来,就把那拨人甩出去,要是能再来一场郭家的大案,我也就认了。”
杨玉道:“那怎么可能,要真到那个份上,只怕有些人就要再脱一层皮了。”
此话一出,两人皆是心头一惊,四目相对之后,皆不再言语。
杨玉虽抱怨,却也不敢懈怠,心急火燎地率众连夜出京,去提审石玺。谁知,他到了毫州后,却得到消息说,石家父子死了!
杨玉又惊又怒,逼问毫州知州颜木:“好好的,人怎么会没了的?”
颜木摊手无奈道:“石玺造孽太多,一经抓回,本地男女老幼无不切齿痛骂,他是活生生被被郡民丁淮踢死的。”
杨玉又问:“那他儿子呢?”
颜木道:“石坚是自缢于狱中。”
杨玉的面色惨白,他道:“还是晚了一步,这下可好了,如何交得了差。”
张允忙道:“石家的仆从何在,我们也可审问。”
杨玉灵机一动,只有人审,能把事情圆过去,不就行了。他最后呈上一叠奏报,的确还牵连了几个人,只是都是凤阳府中的人物,远没有到中央。
朱厚照气得将密奏仍到地上。他想了想道:“叫他们把石家的家眷提回来,交由三法司。”
这是要叫三法司再查一遍的意思。只是,石家父子既死,得来的奏报亦有限。光凭这些,可兴不起大狱。
月池听闻前因后果,情知必是不了了之。自从上次吵过之后,他们又有许久未曾私下见面了。月池想了想,又一次入了宫。
朱厚照彼时正百无聊赖地躺在美人榻上闭目养神。天气渐热了,他也不想再用熏香,而是殿内尽设牡丹。一丛丛半人高的枝株之上,昂然怒放着硕大明丽的花朵。明丽的魏紫,灿灿的姚黄,绣球一般的豆绿,嫣红色的岛锦,竞相芬芳吐艳。而朱厚照的身旁,则是一盆极为素艳的白牡丹,轻盈如楚女朝云,皎洁如姮娥夜月。
朱厚照听到悉悉簌簌的声响,不由皱起了眉:“朕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来打扰吗?”
月池跪在花丛之中:“可是臣来错了?”
朱厚照一惊,他下意识要睁开眼,却在回过神来后,立刻转过身。月池没想到他会是如此反应。她望着他的背影,伸手推了推他道:“这么大的人了,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。”
朱厚照又气又怨:“朕就是长到八十岁,也不和没心肝的人说话!”
月池:“……”
她又和他说了几句,他却只是不理,最后甚至还叫人带她出去。
这次果真是恼得不轻,月池心知,她表现出毫无理由的怀疑,又一次伤了他的心。可这弥天大谎已经撒下来,她便只能继续骗下去。
她想了想道:“我知道是我不对。您一心想着为我好,可我却抱着自卑之心,辜负您的好意。我不是不信您,而是这世上,我能信的只有您。”
朱厚照一怔,他只听月池在他身后轻轻道:“我不敢冒那样的险。我也不愿意把自己好不容易长好的伤口,揭给旁人看。”
外头的粼粼波光,在纱窗上映出朦朦胧胧的影子。朱厚照望着迢迢水色,冷声道:“可你不该那么说话。你其实并不在乎我的感受,对吗?李越,朕亦有尊严,朕不是你的那些傻蛋属下,打一个巴掌,再给一个甜枣,有事钟无艳,无事夏迎春,在朕这里走不通!”
他的心中如明镜一般,石家父子若是还活着,这案子若是很顺利,他未必会这样乖乖认错。
月池一时哑口无言,她问道:“那我究竟该怎么做,您才能原谅我呢?”
朱厚照闷声道:“晚了,心已如死灰,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了。”
月池失笑:“您既已心如死灰,如何却避而不见,您要是肯回头看我,我不信您心中空空。”
第318章 卿须怜我我怜卿
这难道是中华人士天性愚昧,不知善用技术的缘故吗?
他终于还是回头看向她了。他怎么可能舍得一直不见她呢?她在丛中笑着, 数苞仙艳,十里锦绣,总不及她。
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, 可下一刻他就发觉, 她的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讶。这一次的回头,仍在她的预料之中。她永远知道, 怎么拿捏他。他热切的、属于青年人的情感,于是又一次冷却了下去。
他对她的着迷有目共睹。可时至今日,这份着迷却在日复一日的打击、摧残中变了质,参杂了懊悔与怨憎。他本以为他们已经敞开了心扉,他有时真想把李越的胸腔剖开, 看看那颗跳动的心脏究竟是什么颜色。
他是怎么能做到,一边对他说, 他们是唯一的知己,要在一起相伴一生,一边又立马和其他人厮混,一面同他肝胆相照,可转头就能将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,肆无忌惮地用言语来刺伤他、赶走他。只有当他不得不来找他时,他才会又换一张温情脉脉的面孔, 回到他的身旁。
朱厚照微凉的手指抚上她的面颊:“心中有你又如何,朕名义上是真龙天子, 可实际也是肉体凡胎,在你心中,我难道不会疲惫吗?一次一次被你用各种理由推开后, 总有力气孜孜不倦地爬回来。”
月池一愣, 她无言地望着他。朱厚照扯了扯嘴角:“这种推了又拉, 丢了又拣的游戏,你玩不累,可朕累了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,却如重锤一般狠狠击在她的心头。他推了推她:“回去吧。我曾经是真心想做个傻子的,可李越,你怎么连做傻子的机会都如此吝惜呢?”
她没办法给他答案,于是只能又一次不欢而散。
贞筠找到月池时,她正坐在葡萄架下的秋千上。夏日炽烈的阳光将层层叠叠的叶子照得一片透亮。耀眼的光斑投在她的身上,将她雪白的脸颊晒得发红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