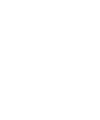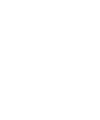相由心生 - 第5节
爷爷的藏书是按照朝代的不同分放在各个书架上的,而且老爷子是用太岁系统来纪年的,这行木雕字表示这个书架上存放的是西汉到东汉的古籍。
按理说,“昭阳大荒落”与“上章困敦”中间是应该留有一点距离从而表示这里是指两个年份的,可是,现在呈现在我眼前的,却是九个字间距都相同的木雕字。
我找了其他书架进行对比,印证了我的疑虑是正确的。
手机光线偏暗,对细节观察的作用有限,于是我用手去摸,果然,在“昭阳大荒落”和“上章困敦”的中间,我摸到了一条裂痕,特别细微,若不是觉得字间距有问题,我大概会觉得这是木头本身的纹理。
我用手敲了敲,声音很空。
我尝试着将“昭阳大荒落”和“上章困敦”上下用力一推,果然,出现了一个暗格。
暗格里面藏有一个暗黄色的丝绸锦盒。
我将锦盒取出来,打开一看,里头是那页之前被我判定成是赝品的王阳明手稿和一本古籍。
这手稿为何要放在这么隐蔽的地方?
我愣了一会,将视线落在了那本古籍上。
古籍的封面有霉菌样,上面画着几个奇怪符号,像是书名。扉页后的纸张是那种自然老化的暗黄,像是观音纸,又好像不是,因为从这纸张的旧度看,起码得有八百年以上,而观音纸最早出现,是五百多年前。纸上是密密麻麻用毛笔抒写的奇怪符号。古籍边上的缝线是新的,像是为了不让纸页散落而缝上去的。
这让我很是疑惑,这么有年头的书,即便是有破损,也应该是请专人进行修补,而不是这样随意缝合。
这还是次要的,让我震惊的是,爷爷居然在上面注释了。在古籍反面上,老爷子写了“周雍摄提格”。
我不由得更加疑惑起来,这缝线和注释,特别不符合老爷子的风格。
老爷子对古籍有一种偏执珍惜,别说是在古籍上注释,就是把古书折一个角他都不肯的。
可就在这时,我听到了书房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。
我下意识关掉手机光源,躲在了书架后方。
书房的门被推开,后厅供奉祖先的烛光泻了一点进来,地面上映出了两个人影。
“我当年确实做错了事,可你们为何现在也不肯放过我,我已经赔上了妻儿,还非得把孙子也搭上吗?”是爷爷的声音,又哑又涩,“是,去瓦屋山找到那块黑玉,就有可能解开这一切谜题,但是,陈豫让的前车之鉴还不够吗?”
陈豫让?这是教授的名字。
“放弃吧,这件事,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。”
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如此沮丧过,而另外那个人,一直没有说话。
两个人缄默了一小会,那人似乎是递了一个什么东西给爷爷,然后先离开了。爷爷看完后,沉沉地叹了口气,也跟着走出了书房。
书房里又安静下来了,我呆坐在原地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回到自己的房间后,我疲惫地坐在床上,脑子里却起了风暴。
已经赔上了妻儿是什么意思?难道,是父亲遭遇到什么不测吗?可他不是好好的活着吗?奶奶也好好的啊!
与爷爷一同进入书房的那个人是谁?明显不是奶奶,今晚外面大门没有打开过的声响,那难道是温湘玉、张继生和陈默三人中的一人?
孙子也搭上?这明显就是说我了,难道,我要出事了?
还有,那句“去瓦屋山找到那块黑玉,就有可能解开这一切谜题”是什么意思?
忽然,我想到了教授给我的照片,连忙找了出来,仔细一看,照片中的父亲,手里确实捧着一个黑色的东西,我记忆中在密道里,冰棺中的父亲手中确实也捧着一块黑色的东西。
这是不是老爷子口中的黑玉呢?
无数的问题汹涌袭来,可我竟是一个也解答不出来,我感觉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,不停下坠,没有尽头。
我揉了揉自己的头,起身打开电脑,将在书房里拍摄的古籍和王阳明手稿照片都导入到电脑里。
我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着古籍上的内容。
古籍上都是稀奇古怪的符号,且没有一个符号是相同的。我在网上查阅了很多古文字,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文字。
好在上面偶尔会出现爷爷的注释,不至于一丁点也看不懂。
古籍大概以六十年为单位成一章节,每一章节后面,都配有一副图画,图画画得很精细,但符号内容却特别简短,仅是寥寥数语。
突然我在爷爷的注释中,发现了‘瓦屋山’这三个字。
我打开手机用网页搜寻着,显示的地理位置是在四川。
我想起张继生说教授几年前也去过四川,那会不会就是去的这个地方?
我继续向后翻了几页,一张插画让我停了下来,我一点点将照片扩大,在不断扩大的画面里,八卦金鸡图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我的心沉重一跳。
一刹那,我好像看到了类似蚯蚓的生物从电脑中源源不断地爬出来。
‘你没错,错的是我们。’
教授信上的内容,又一次出现在我脑海。
我平息了下心绪,继续翻看这本古籍的内容,结果再无所获。
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,可我仍旧睡意全无。
我又想到了那个之前被我判定成是赝品的王阳明手稿,重新审视着上面内容:
“余自知大限将期,不复言秘恐不得间。然谓之玄亦出奇,料诸生难信。丙寅年中,谪官龙场,居夷处困,圣人之道茫无可入,众说纷扰难会于心,遂求静一,久眠村野。忽中夜,入异梦,闻圣贤授业,见庙堂兴衰,观百姓疾苦,识外民甚众,历人世沧桑。荣其道,耻其漏,过尽生灭,须臾转醒。复数日皆思此梦,更以为实,恍若有悟,体验探求,证诸五经、四子,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,圣人之道坦如大路。此之谓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,寤寐中若有人语之”,虽荒唐诡谲,盖非欺也,待后世同道者察。——王守仁,壬寅年庚戌月,于赣州书。”
第七章 送葬
天已经亮透了,屋子里沉寂寂的,倒是胡同外面卖咸橄榄、豆浆油条的小贩,敲着铜碟的吆喝声,一阵阵送来。
一夜无眠,可那页王阳明的手稿,却一直在我的脑袋里盘旋着。
手稿里描述的是,王阳明认为自己在被贬官到贵州龙场时,之所以能够悟道,是跟他做了一场梦有关,是那场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启发。
这篇手稿,我之前就研究过好几天,我一直认为它是假的,因为文章上落款处的时间,是在王阳明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左右,这文章内容本身又是描述了王阳明对自己龙场悟道的解释,如果是真的话,是无论如何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,但我之前翻遍历史,却都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的出处。
可是,这么明显是赝品的文章,爷爷又为何要把它收藏的那么隐蔽呢?
忽然,文章左侧空白区的那个题词引起了我的注意:此文至诚也——任坤。
洪秀全也认为这文章是真的……
这个题词,我之前考究过,是洪秀全的题词,任坤是洪秀全早年的名字。
对洪秀全这个人,我还是有些了解的,他是清末历史上的一个神棍,早年走科举路途没走通,一直抑郁不得志,之后某一天忽然做了个梦,醒来后就号称自己在梦中见了上帝,然后开始创立拜上帝教,之后更是发起了席卷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,给晚清政府造成了沉痛的打击……
等等!
洪秀全也做了个梦?
我心口顿时一紧!
如果这文章是真的,难不成,王阳明和洪秀全这两个人,一个历史上的圣人,一个历史上的神棍,都是因为做梦而改变了人生轨迹?
可即便真的是这样,那这一切,又跟我现在遭遇的状况,有什么关系呢?
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漩涡中,这个漩涡,会将所有的人,所有的事,都卷进去。
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“周沧,是我。”
我起身开门,盛夏的热气在我开门的那一瞬间也一同袭来。
门外站着的是陈默。
陈默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“周沧,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”
我有点意外地看着他,“怎么这么快就要走,进屋说吧。”
在罗汉床上坐定之后,我先开口:“有什么急事吗?没有的话就再玩两天吧,这几天我带你们去逛一下。”
陈默没有吭声,静静地看着我。
“怎么了?”我有些奇怪。
“周沧,”他看着我,似乎犹豫了一下,“我要去给教授送葬去。”
此话一出,我一阵困惑,“教授的葬礼,不是已经在6月12号举行了吗?”
“6月12号那个追悼会,只是走一个形式,真正的葬礼,是他自己规划的。”陈默声音低沉下来,“他给自己选了一块地,土葬,6月21日。”
我的心微微一颤,却没吭声。
“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,”顿了一下,陈默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“是因为教授信中的那张照片。”
他说着,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我,“这是我昨天晚上让人拍摄后发给我的。”
手机里是一张照片,教授躺在石棺中,手上握着小黑玉,那种姿态,跟暗道内水晶棺中的父亲一模一样。
教授与书房密室下的“父亲”,居然都拥有看起来相同的小黑玉,且都以同一种姿态带到棺材中,这显然不是巧合了。
“陈默,教授为什么让你把信交给我,而不是别人?”
我忽然冷静了下来,盯着陈默的黑眼圈,“教授下葬的地点,是在四川的瓦屋山,对吧?”
“我言尽于此。”陈默却没有回答我,站起身来,“湘玉和继生,麻烦你跟他们也说一下,我就不与他们辞行了。”
我也跟着站了起来,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,质问道:“昨天晚上,与爷爷在书房谈话的人,就是你吧?”
陈默看了我一眼,没有回答,挣脱开我的手,径直离开了。
我呆立在原地,一动不动。
屋子外的太阳光慢慢地移入前厅,紧接着,有大门打开的声音传来,陈默走了。
奶奶进屋了,“沧儿,你这孩子真没礼貌,同学要走也不知道去送送。”
“奶,”我看着奶奶,突然觉得一阵心酸。周家现在的情况,她知道吗?
就在此刻,我决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,不管是人是鬼,也不惧赴汤蹈火。
大概是有客在家的缘故,今天的早餐特别丰盛,也很有我们当地的特色,湘玉和张继生赞不绝口。
“周沧,陈默居然不辞而别,太过分了。有多急的事啊,不能等到我们起床。”湘玉一边用筷子夹碟子里那块生豆干,一边说道:“这一次分别,下次见面又遥遥无期了,真是个冷血动物。”
“或许人家真的有急事呢。”张继生笑着说道,“而且,陈默的性格,就是这样的嘛,向来都是我行我素,也就周沧脾气好,才能与他成为好友。”
“不用管陈默了,你们多玩几天,今天天气好,我带你们出去逛逛。”
“周沧,我们吃完早饭,也要告辞了。”湘玉突然放下手中的饭碗,有点不舍地看着我说道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